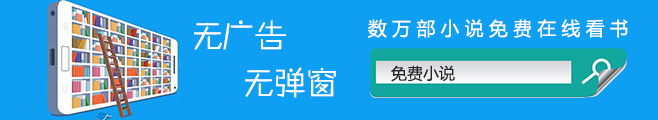高门寒婿的科举路 第258节
而这年,怀佑四年对沈持来说,却是个奔波之年。
九月秋风乍起时,他的祖父沈山过世,享年八十七岁,高寿。他告了假,带全家回秦州府禄县奔丧。
至亲过世,对于官员来说,还涉及丁忧一事,所谓丁忧,是说官员在家中亲丧时辞官守孝,在当朝,丁忧属于自愿,你想辞官便辞了去守孝,不想的话,奔丧后继续当你的官,不作为攻讦他人的理由,是以丁不丁忧全看自己想不想。
但是令所有人震惊的是,沈持上书请求辞官,回乡丁忧三年。
皇帝时年十七,已能亲政,但他看到折子后还是很慌,拉着沈持的衣袖:“沈相,你走了朕心里没底,何况三年太久了,朕和母后都离不开你。”或许是习惯了犹如定海神针一样的沈持在朝,又或许,还有种别的情愫吧,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沈持:“陛下说笑了,陛下知人善任从善如流又聪慧至极,亲政没什么可忧虑的。”
小皇帝十五岁之后他便不再说教,免得爹味太浓惹人嫌弃。
“朕还有很多事情要沈相做主呢,”小皇帝见留人不成,又拿出撒泼打滚的耍赖姿态:“朕还未选皇后,还未成家。”
沈持:“……”
第264章
这是想媳妇儿了?不对啊陛下, 你不是找错人了,该找郑太后说去才是。
沈持在心里嘀咕两下:“陛下,或许……”他有点头大地说道:“您该去问问太后娘娘?”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小皇帝的婚事好似轮不到他张罗吧。
小皇帝眼神闪烁:“沈相你是知道的,太后凤体欠安, 朕哪里敢扰她静养。”
沈持迟疑了片刻:“……陛下可有中意的女郎?臣愿意前往说媒,为陛下提亲。”
“朕……”小皇帝不好意思地笑了:“还未曾见过什么女郎。”
沈持:“那陛下往后多留意着。”小皇帝好像心思又不在娶亲上面, 话又绕回来了:“沈相奔丧后尽早回朝吧,说不准朕明儿就有中意的女郎了, 随时得麻烦沈相去提亲呢。”
顿了一顿他又说道:“对了, 朕打算诰封沈家祖父母, 沈相稍后,朕这就拟旨。”
他打算封已故的沈山为正三品的通议大夫, 沈煌为从三品中议大夫, 其夫人随丈夫晋为同品阶的诰命夫人。
“陛下,臣现下正在风口浪尖上, ”沈持说道:“请陛下不要再给臣以及沈家锦上添花了, 否则坊间又要起议论, 他日臣自会找陛下讨要。”
小皇帝狡猾一笑:“朕可以答应沈相,不过沈相也要答应朕,三个月之内回朝,行不行?”
沈持:“……”他算是瞧出来了, 什么急着娶媳妇儿, 要给沈家诰封, 全是找借口不让他丁忧守孝。
实在拗不过这位小祖宗,他只好答应年底之前回京,接着鞠躬尽瘁当牛马。
……
在一个霜风吹客衣, 红叶傍人飞的九月仲秋日,在京的沈家一家老少头上缠着孝布,乘坐马车快马加鞭往家中赶。除了沈月外,沈莹、沈知朵嫁人后都添了儿女,三五个年幼的孩子坐在一辆马车里,出了京城就在路上打闹起来,一点儿都不理会大人们严肃哀伤的神色,叽叽喳喳的犹如出门游玩那般欢快。
而在另一辆马车里,沈煌则哭得不能自己,嗓子是哑的,眼神是直的……
沈持、史玉皎骑马走在最前头,夫妇二人同样是一言不发。日夜兼程五日后进了秦州府,他们一行人穿着常服,稍事歇息后立即动身上路,谢绝一切拜访。
回到禄县,街肆上的场景与他二十多年前离开时相比,人多了更喧嚣了,百姓的穿着瞧着也更光鲜了。
沈家的马车穿过市井,有眼神好的街坊认出沈持来,驻足高喊:“沈相爷?是沈相爷回来吧?”
沈持从马上下来对他们作揖行礼,哑声道:“是在下。”
知道他是回乡奔丧的,街坊乡亲们赶紧让开路:“相爷节哀啊。”
沈持点点头,又翻身上马打马而过。
回到没玉村村口,远远就看见沈宅上面悬挂着白幡,众人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到了沈宅门口,老刘氏在大儿子沈文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迎出来,沈煌夫妇、沈持、沈月、沈莹、沈知朵等小辈们走到近前跪下去先哭了一通。
也不知是不是人活到一定岁数就什么都看透了,他奶老刘氏看上去并不怎么悲伤,哭完擦干眼泪招呼沈明彰几个小辈:“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沈明彰喊了她一声“太奶奶”,余下的孩子喊“太姥姥”,把个老刘氏欣喜得又抹起了眼泪。
沈家宅子里最显眼的地方摆着的是沈持县试、乡试、会试高中的喜报,上面悬着他状元及第的匾额,沈山在世的时候每日清晨起来都要将这些当成传家宝仔细擦拭得一尘不染,纵然时光过去二十多年,依旧崭新如故。
沈持忽然绷不住,哭了。
史玉皎过来拍拍他的肩头:“节哀。”
按照没玉村的说法,沈山这辈子福禄寿全了——看人家孙子的官位,迟早要诰封,是喜丧,是以办丧事的时候用喜乐吹吹打打为他送行,或许是调子太轻快,冲淡了沈家人的哀伤,过完头七,便见沈家从京城来的小辈们出门到田间撒野去了。
到晚上回家个个像是从泥地里刨出来的一般,少不了被大人一顿呵斥,但第二天早忘了,又撒丫子跑出去叫不回来。
沈持带着史玉皎在禄县逛了逛,又去了史成麟老将军剿匪的隔壁献县,当地还有说书人在茶楼讲起那段故事,不过是把山匪吹成了绿林好汉,朝廷军像个笑话被打得四散逃窜,他们哪里知道当年悍匪将当地百姓抓上山作为人盾,朝廷军怜悯百姓才中了山匪的计,吃了好几次大亏……
“颠倒黑白。”沈持面色冷凝,恨不能将那说书人揪起来质问个清楚。
史玉皎笑笑,对此早已释然:“阿池,算了。”
“等我以后老了,我要编史,哼,绝不能让这种没有下限单单为抓人眼球的民间野史大行其道。”
“相公好志向,”史玉皎挽着他的手臂:“走吧,回家了。”
……
沈持暂离朝堂,有人劝小皇帝趁机夺了他的权,日后再不受他掣肘,小皇帝却大怒,将进谗言之人打了三板子扔出太和殿,私下里遣了名羽林卫,来到禄县请沈持回朝。
他们不知道的是,沈持不在京城,过苦日子的是小皇帝。太后三天两头病着,总是看着沈明彰小时候留在宫里的玩具出神,朝臣事无巨细要跟他奏报,他从五更到夜里二更,没有一刻是闲着的。
他心里没底儿,群臣心里也没底儿。
十月底,西北起了小小的战事,大抵是塞外游牧小国以为沈持离开朝政,大昭朝君臣内讧,因而趁机挑衅,试图探一探虚实,妄图捡几多便宜。
这对于从未识过兵祸的小皇帝和文臣来说,一下子都慌了。连最老练的户部尚书秦冲和都急得团团转,一直问小皇帝:“给沐老将军拨多少军饷?”
小皇帝微愕:“秦尚书是不是记错了,沐老将军要的是粮食和行军打仗的布鞋。”好在朝中贤能不少,缝缝补补总算将西北要的军饷军粮和布匹给凑齐运过去了。
饶是心里知道有沐琨老将军坐镇西北,这仗很快就打赢了,但他还是寝食不安,偌大的皇宫里,除了鹦鹉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后来想到设在宫中的弘文馆,百无聊赖之下将四年前的新科状元薛幼成等人宣进上书房,让他们给他读书,他一遍听一遍同之探讨学问。薛幼成几人不仅读书好,且骑射娴熟,读书之余也陪着小皇帝活动筋骨,几个少年人很快就打成一片。月余后,西北战事平定,朝野上下都松了口气。
小皇帝这时候才明了,当初沈持提议设弘文馆的目的,不光是外人所说的要遣散手中的权力,也有让他培养自己的近臣之意。
在第二次想要催促沈持回朝的时候,小皇帝忽然反悔又叫人将人召了回来:“罢了,沈相多年未归,让他在家中住一阵子吧。”
他要渐渐习惯并学会一点点儿掌控朝政。
……
年底沈持回朝,小皇帝已亲政。
君臣之间没有微妙的拉扯、试探,他从未要过,他也从未说还过,就这样,不知不觉中朝政就到了小皇帝手里。
朝野上下,连同沈持自己也深深地松了口气。这一年,他三十九岁,近不惑。
……
怀佑七年,郑太后为弱冠之年的皇帝萧福满下旨选秀,聘秦冲和的孙女秦氏为皇后,行册封大典。
同年,四十二岁的沈持老蚌生珠,又忙前忙后伺候她媳妇儿去了。跟头一回当爹一般,还是吃吃吃,到史玉皎临产之前,他已胖若两人。
小皇帝又像当年先帝一样揶揄了他几句,送了个清减的药方,他每天泡茶喝,年底,得了个儿子。
儿子生得跟史玉皎相仿,但性子却安静内敛,从出娘胎开始就安安静静地睡着,从来不吵不闹。
跟姐姐沈明彰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次年抓周时,全家都在盼着他抓魁星点斗的毛笔,没想到他却抓起一本医书,捧着爱不释手。
后来,这孩子成人后虽学问极好但却没有入仕,悬壶济世成就一代名医。不过他的三个儿子个个文采出众,先后出任高官,继承了祖父之志,这是后话。
怀佑十四年的春夏之交,郑太后沉疴病重。皇帝亲自来到沈家:“沈相,请你进宫看看太后吧。”
沈持看了眼史玉皎,她似乎从皇帝眼里看出什么,说道:“妾昨儿带着明彰去探望过太后娘娘了,今儿就不陪相爷一块儿去了。”
这个时节,临华殿蔷薇开得正旺,散出满院清香。殿中安安静静的,沈持在门外说道:“臣沈持见过太后娘娘。”
半头白发的老宫女宋莲噙着泪说道:“相爷,娘娘已说不出话来,您近前看看她吧。”
沈持站立不动:“无太后传召,臣不敢逾越。”
就在此时,郑太后忽然清明过来,她说道:“沈相来了?宋姐姐你扶我坐起来跟沈相说说话。”
宋莲:“娘娘……”
沈持等了片刻,殿中的宫女们都退下了,偌大的临华殿里一点微风吹到耳畔都听得格外清晰,他轻声道:“太后娘娘?”
隔着屏风,郑太后说道:“我这一生时常郁郁寡欢,顾影自怜,一半因囿于后宫之中日日如履薄冰,另一半,因为你,沈相。”
沈持听着她的话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太后娘娘,臣有罪。”
郑太后淡淡一笑:“沈相不必惶恐,这是我自己的事,”她摇摇头:“与你没有丝毫干系。”
“就在几年前,我忽然想通了,”她好像赶着要把话说完:“原是我太不知足了。”
“回想起先帝给了我几十年的宠爱,君临天下的儿子,金尊玉贵的太后……哪一样不是天下女子梦寐以求而不可得之事,因而我渐渐把你忘了……只是疼爱明彰好似成了一种习惯……”
她坦坦荡荡地继续说着:“今儿我叫你来,是想把这件事说清楚,也是要交代你,给明彰选一门好亲事,我早为她备好了嫁妆已交代给皇帝,不要让她受委屈……”
沈持听得不觉已是泪如雨下:“……是,臣谨记娘娘凤命,定会护彰儿一生安稳无忧。”
第265章
殿外传来几声黄莺的啁啾, 微风卷着花香拂过,郑太后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道:“多谢你来看我,没什么事儿了, 你请回吧。”
“臣告退。”沈持施礼退下。他走出临华殿的时候,空中一只孤鹤盘旋数圈, 忽而振翅飞往云端,转眼没了踪迹。
当晚, 郑太后仙逝。
次年,在怀佑十五年的春闱中, 来自河东大族董氏之公子, 十九岁的董衡高中杏榜魁首, 新科状元郎风姿秀异,御街夸官时观者如堵墙, 任凭衙役如何鸣锣开道都寸步难行, 后来,有个小厮模样的跑过来高喊:“那边来了个武状元, 可比这个文状元有看头多了。”
围观新科进士的百姓大笑:“朝廷压根儿没开武举, 哪有什么武状元。”
“不信你们瞧——”他用手朝不远处一指。有人还当真伸长脖子看了过去。
只见不远处一行春猎归来的矜贵少年经过, 为首的一人朱红发带飞扬,身着紫衫玉带长靿靴的少年策马经过,他面如羊脂白玉,柳叶长眉入鬓, 雌雄莫辨, 他身后背着弓箭, 马的脚蹬处悬着两只大雁,皆被一箭贯穿双目,可见他箭术十分了得, 惊鸿一瞥让人直呼“玉郎”!
他们眼神凝止,一开始只拿目光追随着他,后来不自觉挪动脚步追逐他而去,早忘了他们是来看新科状元郎的。
涌过去的百姓越来越多,少年勒住马,有点迷瞪地问身后跟着的人:“怎么回事?”
后面的同伴同样想挠头:“今儿放杏榜,他们大抵是围在这里等新科状元郎经过吧。”
九月秋风乍起时,他的祖父沈山过世,享年八十七岁,高寿。他告了假,带全家回秦州府禄县奔丧。
至亲过世,对于官员来说,还涉及丁忧一事,所谓丁忧,是说官员在家中亲丧时辞官守孝,在当朝,丁忧属于自愿,你想辞官便辞了去守孝,不想的话,奔丧后继续当你的官,不作为攻讦他人的理由,是以丁不丁忧全看自己想不想。
但是令所有人震惊的是,沈持上书请求辞官,回乡丁忧三年。
皇帝时年十七,已能亲政,但他看到折子后还是很慌,拉着沈持的衣袖:“沈相,你走了朕心里没底,何况三年太久了,朕和母后都离不开你。”或许是习惯了犹如定海神针一样的沈持在朝,又或许,还有种别的情愫吧,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沈持:“陛下说笑了,陛下知人善任从善如流又聪慧至极,亲政没什么可忧虑的。”
小皇帝十五岁之后他便不再说教,免得爹味太浓惹人嫌弃。
“朕还有很多事情要沈相做主呢,”小皇帝见留人不成,又拿出撒泼打滚的耍赖姿态:“朕还未选皇后,还未成家。”
沈持:“……”
第264章
这是想媳妇儿了?不对啊陛下, 你不是找错人了,该找郑太后说去才是。
沈持在心里嘀咕两下:“陛下,或许……”他有点头大地说道:“您该去问问太后娘娘?”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小皇帝的婚事好似轮不到他张罗吧。
小皇帝眼神闪烁:“沈相你是知道的,太后凤体欠安, 朕哪里敢扰她静养。”
沈持迟疑了片刻:“……陛下可有中意的女郎?臣愿意前往说媒,为陛下提亲。”
“朕……”小皇帝不好意思地笑了:“还未曾见过什么女郎。”
沈持:“那陛下往后多留意着。”小皇帝好像心思又不在娶亲上面, 话又绕回来了:“沈相奔丧后尽早回朝吧,说不准朕明儿就有中意的女郎了, 随时得麻烦沈相去提亲呢。”
顿了一顿他又说道:“对了, 朕打算诰封沈家祖父母, 沈相稍后,朕这就拟旨。”
他打算封已故的沈山为正三品的通议大夫, 沈煌为从三品中议大夫, 其夫人随丈夫晋为同品阶的诰命夫人。
“陛下,臣现下正在风口浪尖上, ”沈持说道:“请陛下不要再给臣以及沈家锦上添花了, 否则坊间又要起议论, 他日臣自会找陛下讨要。”
小皇帝狡猾一笑:“朕可以答应沈相,不过沈相也要答应朕,三个月之内回朝,行不行?”
沈持:“……”他算是瞧出来了, 什么急着娶媳妇儿, 要给沈家诰封, 全是找借口不让他丁忧守孝。
实在拗不过这位小祖宗,他只好答应年底之前回京,接着鞠躬尽瘁当牛马。
……
在一个霜风吹客衣, 红叶傍人飞的九月仲秋日,在京的沈家一家老少头上缠着孝布,乘坐马车快马加鞭往家中赶。除了沈月外,沈莹、沈知朵嫁人后都添了儿女,三五个年幼的孩子坐在一辆马车里,出了京城就在路上打闹起来,一点儿都不理会大人们严肃哀伤的神色,叽叽喳喳的犹如出门游玩那般欢快。
而在另一辆马车里,沈煌则哭得不能自己,嗓子是哑的,眼神是直的……
沈持、史玉皎骑马走在最前头,夫妇二人同样是一言不发。日夜兼程五日后进了秦州府,他们一行人穿着常服,稍事歇息后立即动身上路,谢绝一切拜访。
回到禄县,街肆上的场景与他二十多年前离开时相比,人多了更喧嚣了,百姓的穿着瞧着也更光鲜了。
沈家的马车穿过市井,有眼神好的街坊认出沈持来,驻足高喊:“沈相爷?是沈相爷回来吧?”
沈持从马上下来对他们作揖行礼,哑声道:“是在下。”
知道他是回乡奔丧的,街坊乡亲们赶紧让开路:“相爷节哀啊。”
沈持点点头,又翻身上马打马而过。
回到没玉村村口,远远就看见沈宅上面悬挂着白幡,众人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到了沈宅门口,老刘氏在大儿子沈文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迎出来,沈煌夫妇、沈持、沈月、沈莹、沈知朵等小辈们走到近前跪下去先哭了一通。
也不知是不是人活到一定岁数就什么都看透了,他奶老刘氏看上去并不怎么悲伤,哭完擦干眼泪招呼沈明彰几个小辈:“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沈明彰喊了她一声“太奶奶”,余下的孩子喊“太姥姥”,把个老刘氏欣喜得又抹起了眼泪。
沈家宅子里最显眼的地方摆着的是沈持县试、乡试、会试高中的喜报,上面悬着他状元及第的匾额,沈山在世的时候每日清晨起来都要将这些当成传家宝仔细擦拭得一尘不染,纵然时光过去二十多年,依旧崭新如故。
沈持忽然绷不住,哭了。
史玉皎过来拍拍他的肩头:“节哀。”
按照没玉村的说法,沈山这辈子福禄寿全了——看人家孙子的官位,迟早要诰封,是喜丧,是以办丧事的时候用喜乐吹吹打打为他送行,或许是调子太轻快,冲淡了沈家人的哀伤,过完头七,便见沈家从京城来的小辈们出门到田间撒野去了。
到晚上回家个个像是从泥地里刨出来的一般,少不了被大人一顿呵斥,但第二天早忘了,又撒丫子跑出去叫不回来。
沈持带着史玉皎在禄县逛了逛,又去了史成麟老将军剿匪的隔壁献县,当地还有说书人在茶楼讲起那段故事,不过是把山匪吹成了绿林好汉,朝廷军像个笑话被打得四散逃窜,他们哪里知道当年悍匪将当地百姓抓上山作为人盾,朝廷军怜悯百姓才中了山匪的计,吃了好几次大亏……
“颠倒黑白。”沈持面色冷凝,恨不能将那说书人揪起来质问个清楚。
史玉皎笑笑,对此早已释然:“阿池,算了。”
“等我以后老了,我要编史,哼,绝不能让这种没有下限单单为抓人眼球的民间野史大行其道。”
“相公好志向,”史玉皎挽着他的手臂:“走吧,回家了。”
……
沈持暂离朝堂,有人劝小皇帝趁机夺了他的权,日后再不受他掣肘,小皇帝却大怒,将进谗言之人打了三板子扔出太和殿,私下里遣了名羽林卫,来到禄县请沈持回朝。
他们不知道的是,沈持不在京城,过苦日子的是小皇帝。太后三天两头病着,总是看着沈明彰小时候留在宫里的玩具出神,朝臣事无巨细要跟他奏报,他从五更到夜里二更,没有一刻是闲着的。
他心里没底儿,群臣心里也没底儿。
十月底,西北起了小小的战事,大抵是塞外游牧小国以为沈持离开朝政,大昭朝君臣内讧,因而趁机挑衅,试图探一探虚实,妄图捡几多便宜。
这对于从未识过兵祸的小皇帝和文臣来说,一下子都慌了。连最老练的户部尚书秦冲和都急得团团转,一直问小皇帝:“给沐老将军拨多少军饷?”
小皇帝微愕:“秦尚书是不是记错了,沐老将军要的是粮食和行军打仗的布鞋。”好在朝中贤能不少,缝缝补补总算将西北要的军饷军粮和布匹给凑齐运过去了。
饶是心里知道有沐琨老将军坐镇西北,这仗很快就打赢了,但他还是寝食不安,偌大的皇宫里,除了鹦鹉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后来想到设在宫中的弘文馆,百无聊赖之下将四年前的新科状元薛幼成等人宣进上书房,让他们给他读书,他一遍听一遍同之探讨学问。薛幼成几人不仅读书好,且骑射娴熟,读书之余也陪着小皇帝活动筋骨,几个少年人很快就打成一片。月余后,西北战事平定,朝野上下都松了口气。
小皇帝这时候才明了,当初沈持提议设弘文馆的目的,不光是外人所说的要遣散手中的权力,也有让他培养自己的近臣之意。
在第二次想要催促沈持回朝的时候,小皇帝忽然反悔又叫人将人召了回来:“罢了,沈相多年未归,让他在家中住一阵子吧。”
他要渐渐习惯并学会一点点儿掌控朝政。
……
年底沈持回朝,小皇帝已亲政。
君臣之间没有微妙的拉扯、试探,他从未要过,他也从未说还过,就这样,不知不觉中朝政就到了小皇帝手里。
朝野上下,连同沈持自己也深深地松了口气。这一年,他三十九岁,近不惑。
……
怀佑七年,郑太后为弱冠之年的皇帝萧福满下旨选秀,聘秦冲和的孙女秦氏为皇后,行册封大典。
同年,四十二岁的沈持老蚌生珠,又忙前忙后伺候她媳妇儿去了。跟头一回当爹一般,还是吃吃吃,到史玉皎临产之前,他已胖若两人。
小皇帝又像当年先帝一样揶揄了他几句,送了个清减的药方,他每天泡茶喝,年底,得了个儿子。
儿子生得跟史玉皎相仿,但性子却安静内敛,从出娘胎开始就安安静静地睡着,从来不吵不闹。
跟姐姐沈明彰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次年抓周时,全家都在盼着他抓魁星点斗的毛笔,没想到他却抓起一本医书,捧着爱不释手。
后来,这孩子成人后虽学问极好但却没有入仕,悬壶济世成就一代名医。不过他的三个儿子个个文采出众,先后出任高官,继承了祖父之志,这是后话。
怀佑十四年的春夏之交,郑太后沉疴病重。皇帝亲自来到沈家:“沈相,请你进宫看看太后吧。”
沈持看了眼史玉皎,她似乎从皇帝眼里看出什么,说道:“妾昨儿带着明彰去探望过太后娘娘了,今儿就不陪相爷一块儿去了。”
这个时节,临华殿蔷薇开得正旺,散出满院清香。殿中安安静静的,沈持在门外说道:“臣沈持见过太后娘娘。”
半头白发的老宫女宋莲噙着泪说道:“相爷,娘娘已说不出话来,您近前看看她吧。”
沈持站立不动:“无太后传召,臣不敢逾越。”
就在此时,郑太后忽然清明过来,她说道:“沈相来了?宋姐姐你扶我坐起来跟沈相说说话。”
宋莲:“娘娘……”
沈持等了片刻,殿中的宫女们都退下了,偌大的临华殿里一点微风吹到耳畔都听得格外清晰,他轻声道:“太后娘娘?”
隔着屏风,郑太后说道:“我这一生时常郁郁寡欢,顾影自怜,一半因囿于后宫之中日日如履薄冰,另一半,因为你,沈相。”
沈持听着她的话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太后娘娘,臣有罪。”
郑太后淡淡一笑:“沈相不必惶恐,这是我自己的事,”她摇摇头:“与你没有丝毫干系。”
“就在几年前,我忽然想通了,”她好像赶着要把话说完:“原是我太不知足了。”
“回想起先帝给了我几十年的宠爱,君临天下的儿子,金尊玉贵的太后……哪一样不是天下女子梦寐以求而不可得之事,因而我渐渐把你忘了……只是疼爱明彰好似成了一种习惯……”
她坦坦荡荡地继续说着:“今儿我叫你来,是想把这件事说清楚,也是要交代你,给明彰选一门好亲事,我早为她备好了嫁妆已交代给皇帝,不要让她受委屈……”
沈持听得不觉已是泪如雨下:“……是,臣谨记娘娘凤命,定会护彰儿一生安稳无忧。”
第265章
殿外传来几声黄莺的啁啾, 微风卷着花香拂过,郑太后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道:“多谢你来看我,没什么事儿了, 你请回吧。”
“臣告退。”沈持施礼退下。他走出临华殿的时候,空中一只孤鹤盘旋数圈, 忽而振翅飞往云端,转眼没了踪迹。
当晚, 郑太后仙逝。
次年,在怀佑十五年的春闱中, 来自河东大族董氏之公子, 十九岁的董衡高中杏榜魁首, 新科状元郎风姿秀异,御街夸官时观者如堵墙, 任凭衙役如何鸣锣开道都寸步难行, 后来,有个小厮模样的跑过来高喊:“那边来了个武状元, 可比这个文状元有看头多了。”
围观新科进士的百姓大笑:“朝廷压根儿没开武举, 哪有什么武状元。”
“不信你们瞧——”他用手朝不远处一指。有人还当真伸长脖子看了过去。
只见不远处一行春猎归来的矜贵少年经过, 为首的一人朱红发带飞扬,身着紫衫玉带长靿靴的少年策马经过,他面如羊脂白玉,柳叶长眉入鬓, 雌雄莫辨, 他身后背着弓箭, 马的脚蹬处悬着两只大雁,皆被一箭贯穿双目,可见他箭术十分了得, 惊鸿一瞥让人直呼“玉郎”!
他们眼神凝止,一开始只拿目光追随着他,后来不自觉挪动脚步追逐他而去,早忘了他们是来看新科状元郎的。
涌过去的百姓越来越多,少年勒住马,有点迷瞪地问身后跟着的人:“怎么回事?”
后面的同伴同样想挠头:“今儿放杏榜,他们大抵是围在这里等新科状元郎经过吧。”